白癜风的治疗方法 http://pf.39.net/bdfyy/dbfzl/180614/6329464.html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现代人总是努力成为夏花,但大多数人都忘却了生命是一条线段。
临到终点的时刻,只能被动选择死亡状态,难以落如秋叶。临终关怀中迟到的生命教育填补了一点空白,让临终老人坦然地带着尊严离开。栏目编辑:包工头
.5.3
全文共个字,阅读大概需要15分钟
生死两安,平和中谢幕
3月21日,79岁的琼瑶发表了一封给儿子儿媳的公开信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,希望子女不论多么不舍,都不能勉强留住她的躯壳,让她“变成‘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’的卧床老人。”不论什么情况,不插维生的管子。
琼瑶避之不及的管子却是生命与死亡博弈的最后砝码。五年前,医院ICU病房:文裕章探望脑死亡的妻子胡菁,将她身上的呼吸管、血压监测管等医疗设备拔掉,并阻止医务人员重新插管,导致胡菁呼吸停止死亡。
“我看着她浑身插满各种管子,再想到父亲也做过开腔手术,肺部感染,两个月后死亡”,法庭上,文裕章表情沉痛,“我爱她,我想让她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。”年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,一审判处“拔管丈夫”文裕章有期徒刑3年,缓刑3年。检察院抗诉,广东高院终审裁定,维持深圳中院的一审判决。
如今,人们躺在ICU病房的床上,依靠各类医用管子挣扎求生。在争取“生如夏花”权利的同时,对“死如秋叶”权利的把握却始终在法律、家庭、疾病间盘旋闪烁。
年9月,医院与复旦大学克卿书院联合发布《生命教育、优生优死现状与观念调查报告》。假设自己的生命处于弥留之际,五成以上(53.22%)的受访者选择“不住院,和亲人享受剩下来的每一天”,四成的受访者选择“住院,医院治疗,失去意识后有尊严地离去”,选择“住院,医院治疗,最后即使无意识,插管也要活着”的人仅占5.11%。
当死亡已不可避免,“尊严死”、“自然死”与“等死”,选择权是否还紧握在我们手上?
“老白,我要死了,我爱你”
白墙上的大红中国结和各色油画,透明玻璃窗上的剪纸娃娃,床头桌上的绿色盆景,点缀着北医院素净的病房。
临终关怀专门指对预期生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,通过医学、护理、心理、营养、宗教、社会支持等方式,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站能够尽量舒适、有尊严、有准备地平静离世。
病房里的老人们大多行动不便,除却与时来探望的家属和志愿者进行交流,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,或躺在病床上安然入睡,或静静地望着天花板。天长日久,病友便成了他们最基本的依靠。
病房里共住着五位老人,其中刘奶奶和黑奶奶关系最要好。两个人住对床且都不能动,82岁的刘奶奶性格开朗,长得也很漂亮,患有严重的糖尿病,饭前半个小时要打胰岛素,每次都会让小护士轻一点。年近80的黑奶奶给人看手相很厉害,经常会不停地数数儿,却总也数不明白。黑奶奶很爱哭,每次她一哭,刘奶奶就去安慰她。
▲刘奶奶背靠椅子望向窗外
两位老人经常一起唱歌,比如《小城故事》和《粉红色的回忆》,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偶尔听过几次,“算不上很好听,但那种环境下很动人”,两位老人喜欢讨论《地道战》之类的老电影,或者互相起外号解闷儿。
老白是刘奶奶为黑奶奶起的外号,“你也不黑啊,怎么姓黑呢,我叫你老白吧。”年末,刘奶奶的各项指标开始急剧下降。恰逢《我的诗篇》医院拍摄以“临终关怀”为主题的纪录片,医院,在那段时间里常与刘奶奶相伴。最后的一段日子里,刘奶奶不爱好好吃饭,每次吃饭都要摄影助理一只手搂着她,另一只手喂她,最后近乎抑郁。
年11月的一天,刘奶奶忽然说:“老白,我要死了,我爱你。”
黑奶奶说,“我也爱你。”
十天后,刘奶奶的名字在门前的病友牌上被刮去了。
正午一点时分,医院的老人们多在楼上的病房里午休,大厅里一片岑寂,护工的零星脚步声格外清晰。
一楼大厅旁活动室的柜子上摆满了毛绒玩具,一串串的千纸鹤从屋顶悬到半空,挂着来过此地志愿者的名字和祝福。活动室墙壁上的时间安排表画着各种符号,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活动。“你们待会表演节目吗?春节好久没人来了。”活动时间,老人对志愿者说,然后自己咯咯地笑起来。
▲老人观看志愿者表演节目
在安静的午休时间里,身着灰白色貂皮衣的斌斌是唯一活跃的存在。她大衣里裹着粉红色的连衣帽,手抱浅粉水杯,在大厅与老人活动室之间来回踱步,时而喃喃自语,时而在志愿者身边驻足,反复介绍护工姐姐在前门大街为她买的新鞋,或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小声询问志愿者有没有带糖。
她今年35岁,有着实际年龄的容貌和孩童一般的智商。
庄梦杨仍然记得斌斌住在病房,“我以前经常给她糖,所以后来她见人就会问有没有糖”。
庄梦杨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,医院院办,年12月15日正式离职,“医院工作是我很多想体验的事情之一”。
医院的天里,除了在办公室工作,医院里的人们相处,“老人们都特别简单,久而久之,就会觉得很幸福”。
举重若轻的告别
医院有人去世,病房门口的病人姓名就会被刮去。庄梦杨工作的那段时间里,每日被刮去的名字少则一两个,多则四五个,房间门口写名字的牌子被刮得花白。
医院里,有些人尚未见识过外面的世界,处在咿呀学语的年纪,便已永远失去了成长的机会。更多人则是将历历往事妥善安放,剩下只言片语,就算是最终告别。
年10月25日,是小宝离开世界一周年的日子。
庄梦杨仍记得小宝九个月零六天的那个清晨,她起床看见领导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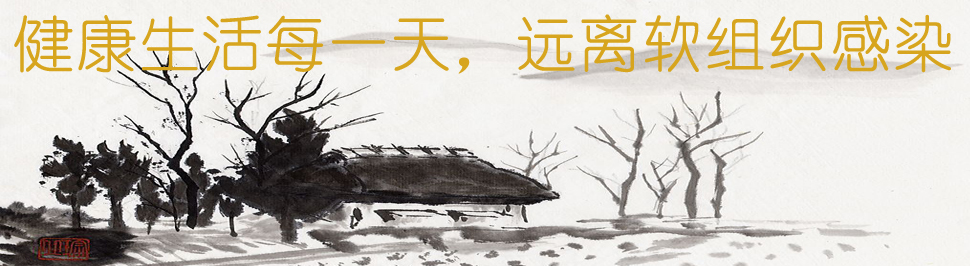




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  E-Mail:
E-Mail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