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个忙碌的星期一上午,臧主任在门诊忙的不可开交,符合住院条件的病人正不断从门诊楼涌向住院部,今天刚刚又有2个新入院的患者急需处理,还有3个病人要在上午10点前出院,明天需要准备7个手术。我和同事们,像往常一样,在医生办公室内像陀螺那样有条不紊的旋转……
突然接到同事小Y的呼唤,我飞奔到护士站,原来又来了一个新的病人+xx床,小Y小声的给我说要做好个人防护,他是艾滋病患者。我赶紧找到这个只有30岁的尚处于人生黄金年华的青年,他正静静的躺在床上,皮肤晦暗,背部微弓,一张饱经沧桑的脸,一副睡不醒极度虚弱的样子;他的旁边站着一位看起来大约有50余岁的中年妇女,他的母亲,这在目不转睛急切的慈爱的望着他。抽完血后,我戴上手套给他进行专科查体,他的右侧阴囊肿的像个煮熟的茄子,摸起来热热的,皮肤表面隆起形成一个大大的脓包……。他小声的说“大夫,谢谢你愿意给我查体。”我说:“我是一个医生,只要你不放弃,我们必竭尽全力,2年前,有个和你类似情况的膀胱癌患者,我们臧主任给做的手术,术后至今一直很好,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,药物治疗不行,我们就尽快给你手术,乐观点,你会尽快好起来的”。
他本是个有着大好前途的充满爱心的阳光男孩,从18岁那年起在北京多次献血,但从某一年起,突然反复感冒、低热,他也一直没当回事。直到年的某一天,他再次去献血时被告知-感染了HIV病毒。“陌生女孩们,多次”给他的生命判了死缓。他的母亲只有他一个孩子,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,他本来是父母唯一的希望和骄傲。这几年来,他的父母一直陪同他与病魔做斗争,天天吃抗病毒的药物,因机体免疫力低引起淋巴结结核、皮肤软组织感染等疾病反复做过2次手术。一路走来,他很是辛苦,父母更是辛苦。在我给他写病历的时候,他的妈妈看他身体虚弱,多次替他补充病史,让他歇会儿、少说几句;他却总是多次冲着她的母亲咆哮“我让你闭嘴,马上闭嘴,你知道什么啊”。他那已有白发的苦命的母亲始终微笑着,态度很和蔼,静静的坐在他的身旁一直紧盯着他。我的心突然好痛好痛,想起史铁生先生在《秋天的怀念》的那段话“双腿瘫痪以后,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,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,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;听着录音机里甜美的歌声,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母亲悄悄地躲出去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,她又悄悄地进来,眼边红红的,看着我。“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,我推着你去走走。”她总是这么说,母亲喜欢花,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,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“不,我不去!”我狠命地锤打这两条可怕的腿。喊着:“我活着有什么劲!”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,忍住哭声说: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,好好儿活,好好儿活……”
病例写完后,他站起来弓着背身体前倾唯唯诺诺的对我说:“大夫,非常感谢;你给我写病历。我虽然生病了,但最近我刚找了份工作,是管理工作,我可以自食其力的。”望着已对生命好似看透的他和他那苦命的母亲远去的背影,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劝慰。
世界上可干的错事有千千万种,但对于一个成年有担当的男性来说,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游戏万花层中,让青春活得看似潇潇洒洒,像某些人所称颂的人不风流枉少年?但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严重亵渎,是对父母对社会极其的不负责任。未来的日子,留给他自己的永远是无尽的悔恨,带给他父母是日日夜夜难眠时刻骨铭心的伤痛。他那可怜的老父母啊,世界上的儿女有几十亿人,但对于他们来说,血肉相连的亲儿子只有这么一个;即便他的生命在慢慢逝去,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日子也许在一天天临近甚至会突然降临。我不敢也无法想象,没有他的家是否还能称之为家;假如没有他,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双亲还能在痛苦孤独中活多少年,两手空空、家徒四壁,没有任何生活保障没有任何亲情慰藉的两颗伤痕累累年老孤独的心,何处才能安放。汝死我葬,我死谁埋?汝倘有灵,可能告我?
无论您在天涯海角,请您洁身自爱;
无论您在何时何地,请您善待父母!
张明庆赞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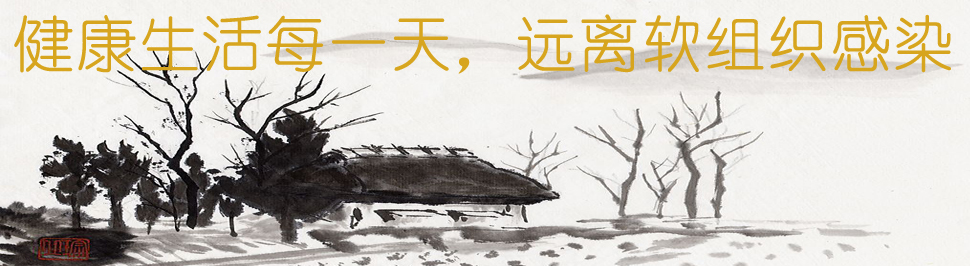




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  E-Mail:
E-Mail: